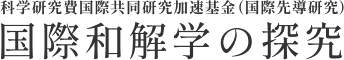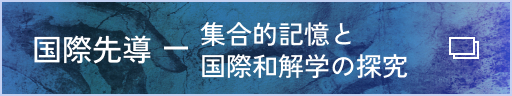「日本宪法学家、汉斯-凯尔森研究著名学者长尾龙一以《和解、忘却、宽容》为题投稿本网。长尾先生现为早稻田大学国际和解学研究所研究员。
长尾龙一(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生活在京都的一位年轻武士,因主家的没落而生活困窘,于是告别妻子远仕异乡的“国守”(律令制时代“国守”为地方行政长官,此后泛指国主大名)。他为了出人头地与良家女子再婚,然而新妻冷酷任性,武士发现自己仍然眷恋最初的妻子,因此陷入自责。国守任期结束后,他将后妻送归母家,就急急赶回京都。虽然家园业已荒废,人迹渺渺,但是妻子的居室透出了一抹光明,打开拉门,武士看到妻子正在灯下缝补衣物。她仍然是那个年轻美丽、令自己思慕不已的女人。武士祈求宽恕,彻夜私语,言曰“自此以往,与子携手”。然而一觉醒来,武士发现自己卧于朽烂的板床之上,有女尸横卧于旁。
这个故事来自《今昔物语》,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1904,日本名字为小泉八云)用英语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取名为The Reconciliation(日译“和解”)。这个故事的梗概,可以说是罪人的忏悔、道歉和宽恕的“内心和解”的典型事例。但是,这则故事正如《蝴蝶夫人》中的平克顿(Pinkerton)一样,仅仅围绕着任意随性的男子的主观期望而展开,已过世的妻子是否真正“宽恕”了他,我们不得而知(也有观点认为,赫恩相信实际上幽灵由异界归来相会)。
这是“一方道歉,另一方宽恕”的道德性非对等者之间和解的事例,未必伴有内心忏悔的象征性的道歉行为,体现为下跪或者(最近)电视画面中那样责任人排成一列低头请罪的仪式。
“通过道歉达成和解”的最新事例,是日本象棋联盟向三浦裕之(Hiroyuki Miura)九段道歉。由于涉嫌违禁使用象棋软件,日本象棋联合会在调查不足的情况下,判罚禁止三浦参加包括“龙王战“在内的正式比赛。而此后不久成立的第三方委员会认定,“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欺诈行为”, 为此,会长谷川浩司和数名象棋联盟负责人辞职。新任会长佐藤康光向三浦道歉,与他达成和解,并赔偿损失。告发者“龙王”渡边明等人也向三浦道歉。
对等者之间的和解仪式,在日益西化的今天以“握手”为代表,黑社会则有“击掌”、“绞手”的仪式,这可以追溯到《魏志 倭人传》中的“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脆拝”的古老习俗。此外,所谓“禊(xì)”和“身涤”、身濯”,即用清水冲洗自己身上附着的秽物的行为,也是对立当事人向神明起誓放弃仇恨的执念和复仇之心的和解的象征。
在对等者之间的纠纷对立中,当事人谋求和解,有着规避纠纷成本的动机。在战况不利时,越晚停战损失越大,正如“不能为了让后背免于伤害而代之以更加重要的前腹”这句谚语所言,谋求停战是源于过重的成本。纠纷如果源于当事人主观上追求正义,那么逃避“一亿玉碎”,将对成本的考量置于正义之上,就会流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敌视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他曾写道,“如果正义以通过某种代价出卖自己的话,正义将不再是正义”,并认为解散国家必须等到处死最后的杀人犯之后(「人倫の形而上学」『世界の名著 カント』加藤新平・三島淑臣訳、pp.474-6。中译《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正义是“同害报复”的“应报刑罚”。
鲁道夫·冯·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 1819-1892)的短篇论著《为权利而斗争》(Der Kampf ums Recht, 1872)中所描绘的英国大陆旅行家的轶事,正是对“纠纷成本”这一观点的否定。他在住宿的地方被骗走了一点儿钱财后,宁愿延长住宿时间,花几倍的费用来挽回所受到的损失。这是因为对他而言,赔偿不仅是钱财得失的问题,还是Recht(权利、法、正义)的问题。
这个故事中有趣的一点在于,在“无视成本贯彻正义”的康德式的正义原教旨主义和视正义从属于效用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之流的功利主义的法律意识的对立中,英国绅士的行动更像是康德式的、德国式的,而对其嘲笑的德国民众一方则似乎是英国式的。这也许是超越国界的西方贵族与西方平民间法律意识不同的问题。
在和解中的下跪及握手等外在的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内在积蓄的憎恶进行清算变得困难,从而引发暂时受到遏制的复仇心理的发泄释放。因此,国家有时会发布“忘却令”。公元前403年,长达一代人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但是这场战争伴随着雅典的内讧,内讧双方势力达成和解时,做出了“不念旧恶”(me mnesikakein)的约定(Xenophon, Hellenika, II,iv,43;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XIX, vi)。
1660年,清教徒革命(不列颠内战)后的国王复辟中,英国国会制定了“免责、忘却令”(The Indemnity and Oblivion Act)。该法案规定,(除部分例外)“必须忘却”(should be forgotten)革命期间的不法行为(injuries)。新王查理二世(1630-1685)采取了宽容以待以实现和解的政策。这项法案正是在他认可下所制定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提倡和解的同时,从历史尘埃中发掘出该“忘却令”的,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其所著《Amnestie, oder die Kraft des Vergessens》 (1949)(Staat, Großraum, Nomos, 1995, pp.218-9),给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纳粹时期为反犹太主义和侵略东欧摇旗呐喊的施密特,竟然在战败后要求人们‘忘却’,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厚颜无耻”(Amnestie是“记忆mnemos”一词的否定形态)。
毋宁说,纠纷对立中的群众心理,无论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卧薪尝胆”,还是针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耻纪念日”,抑或是美日战争的“牢记珍珠港”(Remember Pearl Harbor),“不容忘却”的警句始终是普遍现象。通过法律手段遏制以民族正义感等为背景的仇恨的执念和复仇心理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往往这些仇恨的执念和心理才是民族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
对国际和平最大的威胁之一,是对未收复领土(terra irredenta)的“收复运动”,在英文的维基百科中,“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的条目按照罗马字母顺序,罗列了Afghanistan(Pakistan的部分领土)、Albania(Serbia、Montenegro、Macedonia、Greece的部分领土)、Argentina(英国福克兰群岛)、Armenia(Georgia、Azerbaijan、Turkey、Iran的部分领土)、Austria(South Tyrol)、Belarus(Poland,、Lithuania、Russia的部分领土)、Azerbaijan(Iran的部分领土)、Bolivia(Chile与Brazil的部分领土)、Bosnia & Herzegovina (Montenegro、Serbia的部分领土)、Bulgaria(Macedonia、Romania、Serbia、Greece、Turkey、Albania的部分领土)等等,长长的条目,一直罗列到字母Z(括弧外为要求恢复领土的国家,括弧内为对象地区)。我们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也被罗列其中。这些“收复运动”都是国际纠纷的休眠火山。
对和解而言,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态度。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指出,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会由外部视角拉开距离地重新审视(distanzieren)以往感觉是不言自明的、绝对性的农村式思考和行动方式,从而将以往的视野(Perspektive),纳入到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是知识社会学的开端(“Wissenssoziologie”,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1931, p.666)。他进而认为,相对于将视野局限于树木那样的特定场所的民众,象鸟儿一样来往飞渡于树木之间、综合了各个视野的“自由浮动的知识阶层”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才是知识社会学的承担者(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p.135)。
关于学问的这些议论暂且不论,立足于吸纳了各个纠纷当事人视野的大视野,并将其综合起来的中立的第三方,才能发挥该知识阶层的作用,由第三方角度向双方提出建言,作出警告,并作为实践者起到和解调停者的作用。可以说,国联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正是令这种第三者对和解所发挥作用制度化的组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在英美法一方与德奥作战,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站在德奥一方与英美法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对抗中,日本无法取得英美法德的支持。这种敌我双方的逆转,不仅在国外,在大多数日本国民中也没有得到支持,这一点从众多日本领导阶层遭到恐怖主义暗杀的事实,以及战后日本平稳实现了敌我双方的再次逆转中可见一斑(虽说如此,对德国的转换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大多数民众受到了“昭和民粹主义”的感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死者为16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5000-8000万人,据说,目前每年死于战争和内战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死亡使得憎恶和仇恨的执念进一步积蓄。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普遍性和解”(universal reconciliation)口号的宗教团体也层出不穷。目前,笔者这样的世俗派所思考的,是如何将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作为引导人类走出争斗局限的情感观念所列举的“死亡的恐怖”、“寻求舒适生活所需物品的愿望”、“对通过勤劳获取这些必需品的希望”等和平情感理念进一步放大,抑制霍布斯作为争斗性情感理念所提出的“自我欺瞒的自尊心”(vain glory),并促进冷静地重新审视相互差异的自制与宽容。曾经有某位日本政治家提倡“宽容与忍耐”的精神,这也不正是引导人类历史走向和解的格言警句吗?
(黄斌 译)
生活在京都的一位年轻武士,因主家的没落而生活困窘,于是告别妻子远仕异乡的“国守”(律令制时代“国守”为地方行政长官,此后泛指国主大名)。他为了出人头地与良家女子再婚,然而新妻冷酷任性,武士发现自己仍然眷恋最初的妻子,因此陷入自责。国守任期结束后,他将后妻送归母家,就急急赶回京都。虽然家园业已荒废,人迹渺渺,但是妻子的居室透出了一抹光明,打开拉门,武士看到妻子正在灯下缝补衣物。她仍然是那个年轻美丽、令自己思慕不已的女人。武士祈求宽恕,彻夜私语,言曰“自此以往,与子携手”。然而一觉醒来,武士发现自己卧于朽烂的板床之上,有女尸横卧于旁。
这个故事来自《今昔物语》,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1904,日本名字为小泉八云)用英语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取名为The Reconciliation(日译“和解”)。这个故事的梗概,可以说是罪人的忏悔、道歉和宽恕的“内心和解”的典型事例。但是,这则故事正如《蝴蝶夫人》中的平克顿(Pinkerton)一样,仅仅围绕着任意随性的男子的主观期望而展开,已过世的妻子是否真正“宽恕”了他,我们不得而知(也有观点认为,赫恩相信实际上幽灵由异界归来相会)。
这是“一方道歉,另一方宽恕”的道德性非对等者之间和解的事例,未必伴有内心忏悔的象征性的道歉行为,体现为下跪或者(最近)电视画面中那样责任人排成一列低头请罪的仪式。
“通过道歉达成和解”的最新事例,是日本象棋联盟向三浦裕之(Hiroyuki Miura)九段道歉。由于涉嫌违禁使用象棋软件,日本象棋联合会在调查不足的情况下,判罚禁止三浦参加包括“龙王战“在内的正式比赛。而此后不久成立的第三方委员会认定,“没有足够证据显示欺诈行为”, 为此,会长谷川浩司和数名象棋联盟负责人辞职。新任会长佐藤康光向三浦道歉,与他达成和解,并赔偿损失。告发者“龙王”渡边明等人也向三浦道歉。
对等者之间的和解仪式,在日益西化的今天以“握手”为代表,黑社会则有“击掌”、“绞手”的仪式,这可以追溯到《魏志 倭人传》中的“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脆拝”的古老习俗。此外,所谓“禊(xì)”和“身涤”、身濯”,即用清水冲洗自己身上附着的秽物的行为,也是对立当事人向神明起誓放弃仇恨的执念和复仇之心的和解的象征。
在对等者之间的纠纷对立中,当事人谋求和解,有着规避纠纷成本的动机。在战况不利时,越晚停战损失越大,正如“不能为了让后背免于伤害而代之以更加重要的前腹”这句谚语所言,谋求停战是源于过重的成本。纠纷如果源于当事人主观上追求正义,那么逃避“一亿玉碎”,将对成本的考量置于正义之上,就会流于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敌视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他曾写道,“如果正义以通过某种代价出卖自己的话,正义将不再是正义”,并认为解散国家必须等到处死最后的杀人犯之后(「人倫の形而上学」『世界の名著 カント』加藤新平・三島淑臣訳、pp.474-6。中译《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正义是“同害报复”的“应报刑罚”。
鲁道夫·冯·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 1819-1892)的短篇论著《为权利而斗争》(Der Kampf ums Recht, 1872)中所描绘的英国大陆旅行家的轶事,正是对“纠纷成本”这一观点的否定。他在住宿的地方被骗走了一点儿钱财后,宁愿延长住宿时间,花几倍的费用来挽回所受到的损失。这是因为对他而言,赔偿不仅是钱财得失的问题,还是Recht(权利、法、正义)的问题。
这个故事中有趣的一点在于,在“无视成本贯彻正义”的康德式的正义原教旨主义和视正义从属于效用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之流的功利主义的法律意识的对立中,英国绅士的行动更像是康德式的、德国式的,而对其嘲笑的德国民众一方则似乎是英国式的。这也许是超越国界的西方贵族与西方平民间法律意识不同的问题。
在和解中的下跪及握手等外在的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内在积蓄的憎恶进行清算变得困难,从而引发暂时受到遏制的复仇心理的发泄释放。因此,国家有时会发布“忘却令”。公元前403年,长达一代人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但是这场战争伴随着雅典的内讧,内讧双方势力达成和解时,做出了“不念旧恶”(me mnesikakein)的约定(Xenophon, Hellenika, II,iv,43; 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 XXXIX, vi)。
1660年,清教徒革命(不列颠内战)后的国王复辟中,英国国会制定了“免责、忘却令”(The Indemnity and Oblivion Act)。该法案规定,(除部分例外)“必须忘却”(should be forgotten)革命期间的不法行为(injuries)。新王查理二世(1630-1685)采取了宽容以待以实现和解的政策。这项法案正是在他认可下所制定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提倡和解的同时,从历史尘埃中发掘出该“忘却令”的,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其所著《Amnestie, oder die Kraft des Vergessens》 (1949)(Staat, Großraum, Nomos, 1995, pp.218-9),给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纳粹时期为反犹太主义和侵略东欧摇旗呐喊的施密特,竟然在战败后要求人们‘忘却’,这真是异想天开的厚颜无耻”(Amnestie是“记忆mnemos”一词的否定形态)。
毋宁说,纠纷对立中的群众心理,无论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卧薪尝胆”,还是针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耻纪念日”,抑或是美日战争的“牢记珍珠港”(Remember Pearl Harbor),“不容忘却”的警句始终是普遍现象。通过法律手段遏制以民族正义感等为背景的仇恨的执念和复仇心理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往往这些仇恨的执念和心理才是民族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核心。
对国际和平最大的威胁之一,是对未收复领土(terra irredenta)的“收复运动”,在英文的维基百科中,“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的条目按照罗马字母顺序,罗列了Afghanistan(Pakistan的部分领土)、Albania(Serbia、Montenegro、Macedonia、Greece的部分领土)、Argentina(英国福克兰群岛)、Armenia(Georgia、Azerbaijan、Turkey、Iran的部分领土)、Austria(South Tyrol)、Belarus(Poland,、Lithuania、Russia的部分领土)、Azerbaijan(Iran的部分领土)、Bolivia(Chile与Brazil的部分领土)、Bosnia & Herzegovina (Montenegro、Serbia的部分领土)、Bulgaria(Macedonia、Romania、Serbia、Greece、Turkey、Albania的部分领土)等等,长长的条目,一直罗列到字母Z(括弧外为要求恢复领土的国家,括弧内为对象地区)。我们日本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也被罗列其中。这些“收复运动”都是国际纠纷的休眠火山。
对和解而言,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态度。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指出,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会由外部视角拉开距离地重新审视(distanzieren)以往感觉是不言自明的、绝对性的农村式思考和行动方式,从而将以往的视野(Perspektive),纳入到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是知识社会学的开端(“Wissenssoziologie”,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1931, p.666)。他进而认为,相对于将视野局限于树木那样的特定场所的民众,象鸟儿一样来往飞渡于树木之间、综合了各个视野的“自由浮动的知识阶层” (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才是知识社会学的承担者(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p.135)。
关于学问的这些议论暂且不论,立足于吸纳了各个纠纷当事人视野的大视野,并将其综合起来的中立的第三方,才能发挥该知识阶层的作用,由第三方角度向双方提出建言,作出警告,并作为实践者起到和解调停者的作用。可以说,国联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正是令这种第三者对和解所发挥作用制度化的组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在英美法一方与德奥作战,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站在德奥一方与英美法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对抗中,日本无法取得英美法德的支持。这种敌我双方的逆转,不仅在国外,在大多数日本国民中也没有得到支持,这一点从众多日本领导阶层遭到恐怖主义暗杀的事实,以及战后日本平稳实现了敌我双方的再次逆转中可见一斑(虽说如此,对德国的转换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大多数民众受到了“昭和民粹主义”的感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死者为16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5000-8000万人,据说,目前每年死于战争和内战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人,这些死亡使得憎恶和仇恨的执念进一步积蓄。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普遍性和解”(universal reconciliation)口号的宗教团体也层出不穷。目前,笔者这样的世俗派所思考的,是如何将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作为引导人类走出争斗局限的情感观念所列举的“死亡的恐怖”、“寻求舒适生活所需物品的愿望”、“对通过勤劳获取这些必需品的希望”等和平情感理念进一步放大,抑制霍布斯作为争斗性情感理念所提出的“自我欺瞒的自尊心”(vain glory),并促进冷静地重新审视相互差异的自制与宽容。曾经有某位日本政治家提倡“宽容与忍耐”的精神,这也不正是引导人类历史走向和解的格言警句吗?
(黄斌 译)